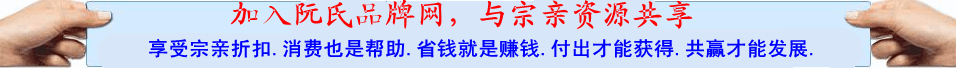阮经天加入我们论坛了?
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会员名:阮经天台湾,我很激动!我想请这位会员发言确认一下,您是否就是大明星阮经天呢?
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!
如果您不是,我们也同样欢迎,能与明星同名也是一番幸事!
强烈要求阮经天现身
强烈要求阮经天现身呵呵 就是不肯出来哟!呵呵 看到阮经天,总有一种亲切感。
我堂弟呀,呵呵
来吧,别害羞,都是自已兄弟,就冒个头吧。
阮经天不算什么,阮凤斌36岁当昆明市副市长了
他是阮氏后人的楷模,向他学习,向他致敬!抗倭名将阮鹗
阮鹗的沉浮枞阳县境内的山北麓,有一座墓园。墓园虽然久未修缮,却气势恢宏,正中为墓室,墓室以下的两旁,从半山腰至山脚,分立着手持笏板与令牌的文臣武将,还有汉白玉雕凿的石象、石马、石羊、石麒麟等。在当地,过去一直流传着一个错误的说法:那是阮大铖墓。其实,墓里安葬的不是阮大铖,而是阮大铖的曾祖父阮鹗。 据清末曾任安庆敬敷书院最后一任山长(院长)的阮氏裔孙阮强等续修的《阮氏宗谱》和史料载:阮鹗(1509—1567),字应荐,号峰,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,官至都御史、浙闽巡抚。明嘉靖年间,倭寇猖獗,浙江沿海一带经常遭受倭寇洗劫与骚扰,敌人侵占岛屿,杀人越货,为害甚烈。当时还是浙江提学副使的阮鹗,敦促诸生习弓矢,练阵法,准备进剿。时隔不久,忽传盗警,杭州戒严,城门紧闭。数十万民众逃至城外,哭声震野,而杭州守城官兵以防倭寇乘机袭击为由拒不开门接纳。阮鹗知道后非常生气,说:“为官本在为民,奈何坐视而不救?”于是不顾同僚劝导,执剑督开武林门,令辎重在左,妇孺在右,依次而入。吃饭时,“兵卒更番传餐,而公则自饭于马上”,整整用了四、五天时间,方使避难的乡民全部进城。百姓感其恩德,焚香祝天:“安得阮公开府以活百姓耶!”之后,百姓又在武林门外建生祠,以彰其德。不久,倭寇又来袭扰,阮鹗亲率诸生壮士出城迎击,斩杀者甚众。
丙辰春,阮鹗调任广西右参政,正要就职,恰逢台、省上报奏章,举荐阮鹗文武兼备,抗倭有功,可大用。于是将其擢升为右佥都御史,提督军务,巡抚浙江。其时,倭寇勾结内奸徐海、陈东率匪兵三万余围攻乍浦,阮鹗多方募集勇士,突围破阵,并潜兵夜袭嘉兴临平山,方解乍浦之围。倭寇遂调转兵力于桐乡,加紧围攻县城。阮鹗料有此举,连夜拼杀进城,他手持宝剑授令知县金燕说:“吾走,则汝斩我,惟汝亦然。”他死守城头,招募冶者“煮铁汁灌城下倭”,与官兵浴血奋战四十余日,为总兵胡宗宪诱杀徐海、陈东赢得了时间。阮鹗随后又督兵乘胜追击,收复仙居,奇袭舟山岛,使倭寇受到了重创。
阮鹗任福建巡抚时,倭寇依然猖獗,为保障福州百姓安全,他移师洪山桥,坚垒防守。其时闽军闻寇丧胆,临阵即溃。阮鹗上任伊始,募兵壮,造战舰,强加操练,以重振军威,故不轻战。不料却遭御史宋仪望弹劾,奏其懦怯畏敌,糜费储饷,图谋不测。朝廷轻信此言,将阮鹗去官解京下狱。阮鹗为官,勤政爱民,深受士民拥戴,途经浙江时,杭城百姓纷纷往岳武穆祠为之祈祷。他带兵,以身作则,“公行军身衣白袷,或臂印而出,或策骑而前。士蓐食则各掇其釜,上饭少许尝之,饱则挹田中水荡口即行”。他爱士卒,“戚继光部兵梁庄时,有一人角中而立,从后曳之,惊见公,顿首,劝无蹈死地。公拊继光曰:‘死地我不畏,所爱者,汝良将耳。’光感奋所至,愿捐躯报公”。阮鹗骁勇善战,“兵不及额,饷不及时”,然“小战则小胜,大战则大胜”。被逮后,福清陷,福安陷,兴化陷,路过兰溪,听说倭寇围攻福宁,仍同官兵直扑倭垒。“火光中望见公红羶白号带”,倭寇惊呼:“浙江阮门提兵亲至矣。”不等天明,纷纷“夺渔舟以遁”。
从后来的李春芳《右佥都御史峰阮公鹗墓志铭》可见,阮鹗之所以蒙冤,一是由于与赵文华、胡宗宪等主抚策略相左,因而受到掣肘;二是后来在福建抗倭捷报频传,“上大加奖异,奈何忌之者力谋倾公,乃指摘公糜费储饷,肆为萋菲,风闻论列,遂被逮至京”。
然而,《明史》的编纂者不辨黑白,捕风捉影,污其惧怕倭寇,敛刮民财,被劾罢官。而其实他是主战派,功勋卓著,遭主抚派嫉妒而削职,是为冤案。阮鹗不仅是一代名臣,又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,战功卓著。后来,其伯子自仑、少子自华多次刺血伏阙上书,“大司徒马公森、大司马霍公冀读而悲之,合疏陈功状,趣两省台使者勘报”,终在隆庆年丁卯月昭雪平反,官复原职,不料阮公竟在这年去世,享年仅五十有九。万历四十二年,皇帝又下《谕祭文》,命直隶安庆知府连继芳宣读。全文如下:
维尔才足投艰,忠期报国。文事必先于武备,内忧克底于外宁。自历轩,遂持节钺。开门纳逃奔之众全活独多;血战保孤危之城折冲更著。肤功已奏于两浙,流言忽起于八闽。三锡未终,百龄奄阻。铜标裹革,谁明薏苡之诬;华表归魂,尚抱松楸之恨。属鲸波之久宴,乃马鬣之新封。爰有加笾,慰兹宿草。英灵不昧,飒尔来歆。
现在,其高度足有丈余,制作精良,镌刻有《谕祭文》的御碑仍矗立于墓园正前方。御碑左右,原有两尊巨龟驮碑,亦刻有铭文,可惜由于年代久远,加之文革摧残,现已坍圮,仅留陈迹。
阮鹗不仅是明朝一代明宦,也是崇尚王阳明“心学”的学者。他早年师从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、著名学者欧阳德为师,对“心学”颇有研究。离京回乡九年,在桐城东乡(今枞阳县)聚徒讲学,孜孜不倦。且著有《礼乐要则》二卷、《枫山章文懿公年谱》二卷。现存《心问》一文,内容崇尚王阳明“心学”,极具哲理与研究价值。
阮大铖是奸臣吗?
阮大铖,字集之,号圆海,安徽人,明万历末进士,官至光禄卿,南明弘光朝官至兵部尚书。才华乱飚,被朝廷“双开”期间,百无聊奈,自编自导戏曲以自遣,一不小心,竟操成“最佳编剧”“最佳导演”。清修《明史》入“奸臣传”。
崇祯二年,明思宗朱由检,也就是崇祯皇帝,即位之后,拨乱反正,万象更新。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被斥逐,阮大铖因党附魏氏而名入“逆案”,今所谓“***集团”,被朝廷“双开”,开除公职开除官籍,削籍为民。这一年,阮氏四十二岁,正当盛年,一夜之间被洗白,自然很不甘心。当时,正值满洲铁骑横行关外,关内也是流贼蜂起,阮氏避居南京,但雄心不死,“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,觊以边才召”,图谋东山再起。这种事,局外人也许无所谓,但局内人却很有所谓。于是有顾杲、吴应箕、陈贞慧等复社名士,共草《留都防乱揭》,也就是“大字报”,贴上街头,要逐他出留都南京。签名者竟多达一百四十余人,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黄宗羲。阮氏曾试图巴结复社名士侯方域,为他包养名妓李香君买单,目的是通过侯公子化解往日恩怨,求得复社名士的谅解。但李香君不买他的账,复社名士更要穷追猛打落水狗,弄得阮氏进退失据无计可施。转眼间,满洲铁骑入关,挥戈南下,江山变色,朝廷易主。复社名士作鸟兽散,各奔前程,或隐居作遗民,或出仕事新朝,但追忆故国旧梦,说到痛打落水狗阮大铖,仍引为生平快事。
可以想象,阮氏彼时彼地何等狼狈。清初戏曲家顾彩甚至认为,阮大铖后来在短命的南明弘光朝东山再起,大搞打击报复,闹得朝野乌烟瘴气,是被复社名士的意气所激。顾氏序《桃花扇》:“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,绝之过严,使之流芳路塞,遗臭心甘。”据孔尚任《桃花扇》,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历史剧,南明弘光朝,仅驻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,即手握重兵数十万,扬言百万,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天堑,如南宋那样偏安百年,但却被南明士林官场的党争内讧玩完了。
读明末遗史,我也有此同感。明末士林多尚意气之争,严君子小人之辨,在野结社,在朝结党,党同伐异,互相攻讦,形同水火。据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,万历后期,就已有齐、浙、楚三党与东林抗衡。各党借朝廷考察推选京官外官阁臣之机,排挤异己培植党羽。东林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,享有“清流”之誉,影响日盛,以至后来成为“阉党”首恶的崔呈秀也曾求入其党,但东林壁垒森严泾渭分明,坚拒其请。各党之间矛盾日深,有些矛盾分歧,也许不乏君子小人是非邪正之争,但更多的却是意气之争,争的是闲气,无关宏旨。后来,甚至为宫廷内部的家务事,如所谓“梃击”、“红丸”、“移宫”三案,也聚讼纷纭,各执一词,纠缠不已。而东林势盛,“与东林忤者,众目之为邪党”。这个“党”,非今日政党之党,而是“朋党”之“党”,利益集团是也。
天启初年,东林党独大,“觝排东林者多屏废”, 而所谓“邪党”更被一一排挤出局。阮大铖原来并非“邪党”中人,他与东林党左光斗为同乡,左为都御史,国家高干,曾推荐其为吏科都给事中,却为执掌铨秉的东林党赵南星、高攀龙所阻,欲用魏大中。魏大中虽为人刚正廉直,但因与高攀龙曾有师生之谊,难免不让人怀疑高氏有任用私人的偏心。虽说举贤不避亲,但在明末士林结党成风的具体语境中,产生这种怀疑非常自然。阮大铖是否作如是想象,文献阙如,不好妄加推断,但自此以后他与东林分道扬镳,却是史有明文。阮氏后来寅缘宦官如愿以偿,遂投靠魏忠贤门下,与东林为敌。魏氏原来也是局外人,他与士林各党皆无甚利害关系,也不偏袒任何一党。三党为顷东林,结成政治同盟,相率归魏氏,并以“东林将害翁”为口实,说动魏氏翦灭东林党。魏氏正是利用士林各党的矛盾,不仅罗织罪名将东林党一网打尽,也将三党势力控制在自己手中,最后满朝文武皆供其奴仆驱使。所谓“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”者也。
今人论及明末士林结社与官场派系,多以“清流”之是非为是非,东林党既有“清流”之誉,则反东林党者非小人即奸臣。这显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。事实上,东林党人固然多君子,如顾宪成、赵南星、邹元标、左光斗等领袖,文章气节,足以震动一时,但反东林者非皆小人。黄宗羲《汰存录》曾引夏允彝之言曰:“东林中亦多败类,攻东林者,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。”夏氏乃明末士林党争的局中人,言必有据,非想当然耳。然士林清流大多偏激浮躁,自居君子,而斥异己者为小人奸臣,且好为危言高论走极端,既不给别人留余地,也不给自己留后路,缺乏雍容大雅的气度与和衷共济的精神。邹元标曾试图打破门户之见,《明史》本传谓:“时朋党方盛,元标心恶之,思矫其弊,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。”但不能为同党中人理解,至被讥为首鼠两端。东林党人之高自标举唯我独尊,精神可嘉,但不能广结善缘,结果是为林驱鸟为渊驱鱼,众多不得志于东林者,相率归附宦官魏忠贤。即以阮大铖而论,他阿附魏氏并非有意为恶,不过是出于为个人政治利益考虑的机会主义。而且,走宦官路线是明代后期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。万历朝的名相张居正,就是与宦官冯保内外联手,击败前任高拱并取而代之。而东林党排挤三党,也曾借助宦官王安的一臂之力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这是官场上的政治策略,无可厚非,但何以阮氏走宦官路线即成不可原谅之罪恶?而且,阮氏既非魏氏死党,也非“阉党”首恶,最多不过是同流合污的爪牙。
事实上,此公深知官场之风云变幻一朝天子一朝臣,所以在魏忠贤时代,表面上俯首贴耳曲意逢迎,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据《明史》本传,阮氏每谒魏忠贤,辄厚赂其门人,还其名刺,以免留下巴结宦官的证据。魏氏不过暂时得势,他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而且,他两度请假乞归,在官日前后不足半年。如此首鼠两端,无非是怕陷入太深,更怕趟“阉党”的浑水,日后被东林党人清算。值得一提的是,崇祯元年,宦官魏忠贤被斥,阉党领袖崔呈秀乞归,时局尚不明朗,阮氏给京中挚友杨维垣寄去两封奏疏,其一专劾崔、魏,另一同劾崔、魏与东林,谓:“天启四年以后,乱政者魏忠贤,而翼以崔呈秀;四年以前,乱政者王安,而翼以东林。”他传语杨氏,若时局大变,上前疏,如未定,则上后疏。总之,是见机行事看风使舵,无所谓原则操守可言。这种官场心态,明末文人多有之,非阮氏一人而然。他们逢场作戏随时俯仰曲学阿世,事后又作天真无辜状,谴责奸臣当道一手遮天,而自己则是一时糊涂误上贼船。或谓中国士林愚昧,其实这正是他们的世故。
阮大铖深谙这种逢场作戏的官场世故。所以他在削职为民后创作的戏曲,几乎皆是喜剧,场面热闹妙趣横生,既无徐渭式的骂世主义,也无汤显祖式的悲观主义,而是所谓“错误的喜剧”。剧中充满“误会”、“巧合”,好像人生的种种矛盾种种冲突,皆由“误会”而生。这是否为阮氏心迹的表白?东林党与他的矛盾冲突乃一场误会?不得而知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写杨文骢为其游说复社名士侯方域曰:“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,原是吾辈。后来结交魏党,只为救护东林,不料魏党一败,东林反与之水火。近日复社诸生,倡***击,大肆殴辱,岂非操同室之戈乎?”这种事后辩解,当然不能服人。阮氏之党附魏忠贤,为其爪牙,虽事出有因,但绝非为东林内援,则毫无疑问。这里有明末士林党争的背景,也有人在官场不得已的苦衷,更有古今士林人皆难免而在明末恶性膨胀的根性。其实,包括有“清流”之誉的东林党在名利场中,也出了不少翻云覆雨的“伪君子”,这在阮氏看来,无异于五十步之笑百步。张岱曾谓:“其所编诸剧,骂世十七,解嘲十三,多诋毁东林,辩宥魏党,为士君子所唾弃。”张氏乃当时见证人,所言自有道理。但我们今日读阮氏的《春灯谜》(又名《十错认》)、《牟尼合》许显纯诬以受杨镐、熊廷弼贿,涟等初不承,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,冀下法司,得少缓死为后图,诸人俱自诬服。”我相信东林诸君子的人格,绝不可能为中饱私囊而拿政治原则个人清誉作交易,但在明末士风堕落学术腐败吏治腐化的大环境下,谁还相信你廉洁自律出淤泥而不染?魏氏这一招也真夠狠毒:贪官污吏人人憎恨,既加之罪,何患无辞?我想当年东林党招权纳贿的罪状,以圣旨名义昭告天下时,不明真相的民间百姓也许还拍手称快。否则魏忠贤何以因诛东林而得到民间士庶拥护?据《明史?阉党传》,浙抚潘汝桢之在西湖为魏氏首建生祠,乃“徇机户请”。机户,就是今所谓“工人阶级”,普通百姓而已。假民间百姓之名,而行阿谀奉承之实,这本来就是文人政客惯用的伎俩。
魏忠贤虽不幸而为文盲,赌场失意,不惜自宫,以人生为赌注。但他不是弱智。集体献媚的全国运动,是否真代表士林民间的心声,我想魏氏一定心知肚明,偷着乐。他是真正看透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士林的劣根性。士林中人虽好读书,圣贤书,但读书不一定能增长智慧,何况是迎合“体制”的读书?八股取士造就的读书人,能如东林诸君子者本来就是风毛麟角,而东林又多意气书生,宜乎其被一文盲宦官玩于股掌之间也。
看了明史你会生气,皇帝不是皇帝,文人不是文人,怪不得老毛生气 希望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也能加进来,O(∩_∩)O哈哈~ 如果他了解到我们的站,一定会加进来,呵呵 6楼的历史搞个电影出来有前途。
页:
[1]
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