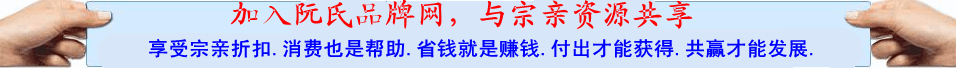悼念堂姐阮亚娣
堂姐亚弟
农历甲午七月初二是堂姐亚娣三周年的忌日,作为娘家人的堂嫂,头日在胜山庙做道场,告慰亡灵,我自驾车专程送妻参与。由于“胜陆公路”造高架封闭施工,我们从逍林镇区绕道,穿过胜山前的村落,到达大湾的胜山庙化了半个多钟头,那时母亲、两个堂兄堂嫂、我的两个妹妹等都到齐,祭祀活动已经开始了。我是无神论者,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,烧香念佛拜菩萨,只是活人们的一种纪念形式,安慰自己的心灵而已。送达后,我就回单位上班了,没有参加僧人们诵经祈祷活动,也没吃斋饭。
堂姐其实与我同龄,都是乙未年出生,因为她的出生日子在农历九月初十,比我降生早近两个月,即或双胞胎,一先一后落地,也得是姐弟相称,可是我在现实生活中,从来也没有叫过她一声姐,习惯于直呼其名。小时候,她的力气比我大,曾记得我们十岁那年,三姑妈生产后,父母们忙于集体劳动,无暇走亲戚,让我们俩挑着两板篮的糖、面、鸡蛋等物品,去东二七大队送“生姆羹”,八华里的路程,我只能挑一小段路,也是腰身歪斜,似千斤重担压肩的颤栗,就调换给她,大多数路段都是她挑着。后来父母和大爹嗔怪我,算什么小伙子,这区区几斤物品呢!我还狡辩说一根竹扁担也有份量呀!这件事一直戏说到我们长大。我们老家有句歇后语:“六指末头打巴掌——加一”,意思为特殊等待。亚娣出生时的右手大母外侧有畸形小指,俗称“六指”,在7、8岁时做了外科手术,切除了小手指头,手术很成功,恢复得也很快,不但没有影响生活,就连痕迹也不是很明显。
1976年11月26日的那天,晴空万里,蓝天白云好像有意来祝贺人间的喜庆,这是亚娣出嫁的黄道吉日,喝喜酒的远亲近邻都聚集在下二灶我的老家,人们穿梭般的身影进出屋内房外忙碌着,橱房里更是一股热气腾腾的状态,到处弥漫着蒸米饭的飘香和烧菜时的油鲜味,有的人互敬香烟聊天,有的嗑着瓜子大声说笑,更有孩童们的衣兜里塞满了爆米花、盐炒烧豆、炒花生等物,在人群中钻来窜去,堂屋里许多人勤快地搬桌摆凳、分筷放碟、添酱油加醋、放酒杯安酒壶,尤其是女眷们拥进亚娣房间,黑压压地围绕在她的床前,整这理那、梳妆打扮,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。不一会,大家簇拥着亚娣到早已停泊在七塘江河埠头,乘船上“轿”,载着新娘子的农船离岸远去,人们陆续返回屋内喝喜酒了,一番都是喜气洋洋的忙碌。亚娣结婚还只有22虚岁,男方比她还大4岁。按当时的《婚姻法》,女18足岁、男20足岁就可以领结婚登记证书,算合法夫妻了。
按当地的传统说法,亚娣的婚姻是亲上加亲。新郎是崇寿公社东升大队龚复树,我奶奶同胞姐姐的孙子,我们的爷爷与男方的爷爷是嫡亲的两连襟,都拥有施家同一个丈姆娘和丈人,两家属于老亲戚,到了亚娣的辈份,属于表表兄妹关系连姻的新亲戚,也就是俗话说的“表兄妹当老宁(人),亲眷省两份”。由于我爷爷、奶奶离世得早,留下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,最大的亚娣爸爸还只有19虚岁,6个未成年的孤儿人家,不但不懂得人情世故,而且也没有交往的经济能力,所以很少有家人和亲戚走动,表亲戚更加疏远,以前基本不往来,因亚娣的婚姻,两家的亲热度升温了,凡是家里有什么喜庆或是节假办饭,总是礼尚往来、请吃堂饭,包括早已单家独立的我们。
上世纪70年代的家庭伦理,虽然说是到了没有封建制度束缚的新社会,但是有些传统习俗还是要遵循的,尤其是家务劳动、尊敬长辈和家庭成员方面,新媳妇也有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比如:新媳妇烧早饭。过门后的第二天早晨,新媳妇要早起,在家人还未起床前,要上灶烧火煮饭,把全家人的早餐准备就绪。这既是新媳妇家务劳动能力的考验,也是勤劳的主妇持家的开始。
我堂姐夫家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,上有公婆和奶奶,同辈兄弟姐妹有七个,亚娣进门是第三房媳妇,大哥、二哥已成家,还有了第四代,一家吃饭十几个人。新婚第二天早餐,婆婆和二嫂起得早,灶前灶后主要是她们俩在忙碌,亚娣只在灶堂里添些柴火,一个月后,正式轮到亚娣当班做饭菜了,虽然亚娣十三岁开始能上机织布了,懂得会做缝补浆洗、烧茶煮饭的家务事了,曾受大妈的夸赞“小人做了大人生活”。可是娘家的烧火煮饭只6口之家,多数时间还有嫂子和母亲,现在的家庭不但有10几个人,而且独立操作,轮到需要一个月时间的早起和晚睡,更让亚娣倍加小心的公公是个讲究家道尊严的人。
亚娣每天凌晨起床,一锅开水,一锅饭菜,双管齐下,10几个的饭菜,需要二尺二寸的大镬烧煮,用双层的蒸笼煮菜,烧火时的大风箱要拉得不停,没有个巴小时的忙碌,煮不好饭菜。奶奶上了年纪,早晨洗漱在房间里面,亚娣烧好饭菜后,还得打起洗脸水,送到奶奶房里,随后再打扫厅堂和自己房间,几个来回,一家人开始用餐,早餐后还得把那么多的碗、瓢、勺、筷、镬、桌洗刷干净,再出门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。由于亚娣的善良和勤劳,一时成为东升大队社员们的美谈:“龚家娶了个漂亮媳妇”、“龚鼎良有福气,娶了个贤慧媳妇(龚鼎良是亚娣的公爹)”。
堂姐夫是先天性的高度近视眼,父母从小让他学了泥水匠的手艺,当时社会的经济落后,尽管他参加了崇寿公社的建筑队组织,泥水需求量很少,赚来的钱除了向生产队上缴记工分之外,所乘无几。后来,他自己单干给老百姓做散工,靠勤劳和善良取得了社会信任,为了增加收入,他开始带徒工,不仅带了邻居的男青年,还让自己第五兄弟也学会了泥水师傅。俗话说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。过去的手工业劳动业务量小,多一个手工业者多一份行业竞争,尤其是近距离的同行,更是“同行三分亲,七分仇”。 竭泽而渔,我堂姐夫竟然犯了手工业师傅的大忌,为后来的兄弟失和埋下了祸根,这是余话。
小夫妻有了下一代,家庭责任感陡然增加。堂姐夫以慈溪县第三建筑公司崇寿工程队的名义,在宁波西郊电子元件厂承包到了职工宿舍楼的建设工程,那是慈溪建筑行业进军宁波市场的先头部队,他组织了10几个打工者队伍,按厂方的要求自己设计,自己组织施工,包工包料,独立核算。一年多以后,工程全部完工,近10万元的盈利,衣钵满归,回乡后,建造了三间两层,中间局部三层的新式楼房落成。当时,在“万元户”追求目标年代,我堂姐家耗资5、6万元,一幢“品”字形平楼在“人”字形瓦屋村落里,显得鹤立鸡群,非常醒目,大爹夸赞女婿能干,众兄弟们敬慕有嘉,凡从七塘公路通过的人,没有一个都不刮目相看,成了当地先富起来的家庭。
随着农村棉粮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,自由种植和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民放开了手脚,勤劳致富,财力积聚,农村掀起了建楼房的热潮。龚复树和亚娣看准了商机,以堂姐夫泥水匠出身的手艺,添置设备,组织劳力,在屋前道地上办起了预制品厂,生产水泥楼板,销售给需要建楼房的农户,生意红火,预付款纷至沓来,五孔板生产供不应求,利润丰厚,夫妻俩东奔西跑,忙内忙外,风尘仆仆,付出总有回报,家庭财富聚集,手头资金阔绰,“亚娣家成老板了”的赞言也在我家传开。
亚娣深知自己没有文化的困惑,懂得知识能改变命运的道理。夫妇俩努力让两个孩子认真读书,好好学习,培养成长,练就本领。亚娣一边协助丈夫在预制品厂备料、生产、销售等方面拾遗补缺的工作,另一边操持女儿和儿子的生活起居、学习监管。尤其是央青的艺考,他父亲一路从杭州、金华的陪伴,一次次的参与和生活上的照料,费尽了心血。那年,立庆骑摩托车出事故,三人受伤送医院急症,其中舟山的同学粉碎性骨折,转院舟山治疗,家人上上下下的忙碌,真是鞠躬尽瘁啊!
功夫不负有心人,女儿央清大学毕业后,考进宁波市海曙区房管局工作,结婚成家。儿子立钦大学毕业了,总算结婚成亲。仅管夫妇为操办儿女的婚事,费神又花钱,可是内心总是充满喜悦和幸福,祈望未来的大家庭,传宗接代,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。
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,第一轮农居楼房几年之后,被现浇板所替代,半框架结构、全框架结构房屋也在农村兴起,水泥预制板纷纷退出市场,泥土烧制的红砖转用水泥砖块,市场需求猛增。龚复树迅速转产,由生产五孔楼板改产水泥砖,添置生产的机械设备,与大兄弟合作,共同出资,再生产,也曾一度兴旺。可惜,好日子不长,由于经营上没有形成规模和管理上的意见分歧,造成兄弟反目,亏损严重而倒闭。
身心疲惫的夫妇,在市场经济中退下阵来,俩人无所事事地融入了左邻右舍搓麻将的队伍。有时屋里大堂一桌不够,小厅再设一局,麻将两桌头,白天搓好,夜里继续,烧菜做饭来不及,冷菜泡饭方便面解肚饥,结果是输钱不多,光阴流失,生活失去了规律,身体缺少调养,生物钟紊乱,长期疲惫,精神懈怠。
几年下来,夫妻俩自己也认为不能这样了,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打算改变日常的生活内容。龚复树在杭州湾新区的企业找了一份做门卫的工作,每天用电瓶车往返,成了打工仔,亚娣也以家务为主,领养照顾孙女和外甥女,有时还赴甬照顾外甥囡,过起了琐碎的晚年生活。
2006年9月的一天下午,我还在单位办公室,突然接到妻子的来电,说让我询问一下周医生是否上班,龚复树在骑电瓶车下班回家的路上捽了一跤,马上要找骨伤科医生。慈溪市中医院的骨伤科原主任周国民医生,是我多年来交往的老朋友,我们家一旦有什么头痛脑热的都找他,虽然他是应征入伍之后学医,转业到东安乡卫生院工作,学历、文凭并不高。但是临床经验和医疗技术还是相当的了得,中医院骨伤科的社会名望不亚于慈溪人民医院。经姜婉珍联络下,龚复树很快得到周医生确诊为左小腿脚骨折,需要住院治疗,得动手术,打钢钉、绑石膏固定、静养,亚娣自然要全程陪护。百病有百药,独怕病因摸不着,对症服药,百病消散。三个月后,龚复树可下地行走,恢复健康,精神饱满,又过上了正常生活。
2008年9月2日傍晚,我们夫妇俩刚散步回到家里,电话机突然响起,从电话里得知:龚复树患了重病,半身失去了知觉,昨晚从慈溪人民医院转到了宁波李惠莉医院,昏迷不醒。第二天一早,我从银行里提出一万元现金,与妻子一起自驾车赶到宁波医疗中心(李惠莉医院)住院部。经询问得知,龚复树患恶性脑瘤,不动手术就此瘫痪,无法行走,开颅手术也只能切除大部分瘤子,无法清除大脑夹缝中的瘤组织,有6个月的生命延长期,并且必须到全国最权威的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手术。突然的恶噩,让家人和亲戚们惊愕了,面对残酷的现实,谁也不忍心让一个活生生的亲人就这样离开。作为儿子的立钦,家里没有现钱积蓄,女儿央清刚按揭购买好房子,眼看58虚岁年龄的父亲,走到了阎罗王殿的门口,无论如何总要竭尽全力挽救生命,多活一天也是好!央清决定举债抢救父亲,即使只活半年也要孤注一掷,请求院方马上联系上海华山医院,做好手术准备,立即转运上海救治。我把随带的1万元交给了亚娣,书英也从家里拿来3万元,央清带上银行信用卡(可偷支),租用救护车,直送抵沪。
手术很顺利,回家后马上可以下地走路了。那天,我们去看望他,脸色红润,神采飞扬,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病史和感受,并来回走动、挥臂举腿向我们展示,他的行动完全自如,恢复正常,真的象没有生过病的人一样。虽然,医生告诉过我们这是治表不治本的措施,我们在他的面前还是靳钉截铁地肯定,彻底治好、完全健康。
半年后,不出医生所料。龚复树的半边手脚又出现异常,脑瘤病情又复发了,再次到上海华山医院住院治疗,慢慢地病态严重起来,医生也无回天之力,返回家后又到慈溪人民医院作保守疗法,缓释精神痛苦,昏迷了一些日子之后,于2010年5月19日离世,正如他自叹的只有岳母59岁一样的寿命。虽然病魔没有让你表达语言,但是您对子女的爱和家庭的未来是多么的留恋和不舍。
料理出丈夫丧事后亚娣,身体的劳累和精神的严重打击,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,又要奔波在慈溪、宁波两地,照顾孙女和外甥女的生活,依然忙忙碌碌。
年底应邀来佳先家客居,自诉腹部有硬块、伴有大便不通的症状,还追忆在复树患病期间曾经出现,还有便血。经众亲的劝说,在附近的地方医院打针服药,也不见根治。春节过后,又出现了10几天拉不出大便,央青接她到宁波医院诊断,确诊为结肠肿瘤,转杭州邵逸夫医院作手术治疗。
住院期间,我与妻子自驾车到杭州看望慰问,得知她的病情已到结肠肿瘤晚期,虽然作了肿瘤切除手术,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它器官,前景不容乐观。
亚娣出院后,在家里继续打针服药作保守疗法,约过了半年时间,咳嗽、疼痛不止,只得住进了慈溪中医院,我们几次看望,只见得她身子渐渐地消瘦,症状忽轻忽重,好在她的乐天派性格,精神上并没有太多的悲怆,在你弥留的日子里,从眉梢眼角分明表露出对生命的热爱,对子女的牵挂和忧虑,我们唯有暗自落泪。2011年8月1日她也撒手人寰,享年56岁。我的同龄人,早我两个月来到世上,且这么早就离我而去,写到这里我的心头涌满悲哀,你节俭勤劳地成家立业,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拉扯大,没有坐过飞机,也没有游览大好河山,还把女儿陪伴唯一的坐高铁去厦门念念不忘,你跌跌撞撞的人生路,坎坷艰辛的一生,就这样短短地结束了,我只有在这里称呼你姐姐!
短短的两年时间内,一对勤劳的夫妇相继离世,据《慈溪市志》公布2010年平均寿命高达79.52岁的时候,他们且都没有活到自己的正寿(60岁),可惜啊!
父母相继亡故,子女的财力、精力都被彻底的掏空,亲戚们也牵肠挂肚,成了医院的常客。仅管子女们已经成家,但是失去了双亲,没有高堂的家庭,象刚出巢的稚鸟,断了回望的老路,只有在墓地相会,心灵的落寞和精神的无助是多么的惆怅!
以此文作为我的哀思,让亚娣夫妇在天之灵永生!
堂弟: 阮 万 国
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阮亚娣(1955.10.25-2011.8.1),龚复树(1951.-2010.5.19),生有一女央清,一子立钦。
同悲{:1_8:} 追忆抹不去的记忆,愿亚娣夫妇永生! 阜阳阮俞古 发表于 2015-10-12 05:57
追忆抹不去的记忆,愿亚娣夫妇永生!
感谢宗亲的眷顾,百姓人生一草秋,劳碌一生病来袭,无可奈何枯萎败。 愿生者坚强, 逝者安息!
页:
[1]